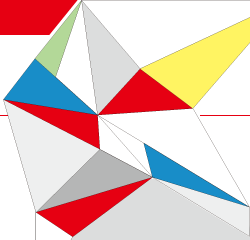☉郭力昕 (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講師)
政治活動中的選舉,如果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在選舉活動頻繁的台灣,它已經快要變成一種生活目的了),那麼選舉美學就必然是生活美學與文化水平的映現,而不太可能外於我們的生活或文化內涵,獨自存在著一個叫做「選舉美學」的東西。
台灣選舉文化中傳統的賄選、暴力與分贓,加上新添的綜藝、秀場
與狗咬狗,都是我們平日生活內涵與內容的一部份。它的光怪陸離與我們的終至於見怪不怪,如同張小虹教授所言,是台灣文化「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同時並置」之下的獨特景觀。我稍做修改的是,從普遍的角度來看,這種並置是前現代與所謂「後現代」的混合,而獨缺「現代性」-我們文化/社會中的理性、秩序與進步性,表現在哪裡?
在這個尚未扎實的、深刻的經驗過「現代性」文化洗禮的島嶼上,九○年代以降,忽然節慶式的大量湧現著「後現代」的辭藻與景觀,正如張小虹的質疑 ,只是一種不具有內在顛覆性的金光假象。因為,這些浮面的影像底下,仍然有太多前現代的實質樣貌。換句話說,台灣這些擬似後現代式的選舉秀場與猴戲,只是包裝了一個大體上前現代的政治與文化體。這樣的一種包裹,其實恐怕正好鞏固了台灣的「前現代」文化情境,讓它繼續頑強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 與社會之中。
從這個基調來觀看台灣聲嘶力竭、視聽混亂的選舉文化,則我認為非常不堪地,它呈現的美學,就只是一種「地攤文化」的美學。台灣文化的某種總的精神面貌,容我妄言,即是一個地攤文化。什麼是地攤文化呢?在形式上它是永遠的臨時與野台狀態,隨時可以收攤、拆台、換個地方再擺;它是一種無奇不耍、無貨不可賣(無論是機車修理行兼賣貢丸湯,或是「保衛中華民國」,與「我是正港台灣人」兩種商品並列櫥窗)的江湖郎中文化,與一種「充滿了聲 音與憤怒、卻毫無意義」的煽情叫賣文化。
在內涵上,地攤文化是「先/現幹一票再說」的文化。它是現實功利性格的極度呈現,因此它毫無原則、格調或信念,也毫無興趣做固定的、長遠的投資、規劃與經營。所有的力氣與目標,就在賺眼前這一筆、贏今天這一場。於是,擺地攤的人固然充滿投機媚俗的身段和語言,以吸引更多顧客和現金,逛地 攤的人也沒有什麼品牌或理念的忠誠度,在眼花撩亂之中,一切跟著感覺與情緒走。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宣稱是一個「清流、理想」的政黨的堅定支持者,會由於集體非理性的迷戀上一種「情緒商品」-無論是一個臉孔、一個口號或一個自己嚇自己的心理-,為了急著贏眼前這一票(甚至也已經備妥 各種自我合理化的理由,為自己的率爾背叛那個充滿理想與人才的政黨,找到了釋除歉疚感的下台階),而輕易的掉頭轉檯。政黨的理性成長,政黨政治的穩定建立,恐怕從未出現在這些「逛地攤」的人們的意識或興趣之中。
在政治的夜市地攤(無論攤位是中正紀念堂或中山足球場)中瀏覽「情緒商品」,乃是台灣一向以來的選舉美學。在擺攤與逛攤的過程中產生的視覺、噪音污染與文宣垃圾,是此種「地攤美學」的必然副產品。有論者批評這些破壞環保、「老片新看」的難看選舉劇碼;但是,卻認為「金達尼號」與「紅色競 選公車」是今年選舉中「提出新美學觀且富文化意義的兩項作品」,因為它們「運用台灣人共同的文化經驗(電影『鐵達尼號』,貌似電子花車的外觀,搭公車),創造了一個空間上流動的輔選中心和競選總部」。
我恐怕難以同意後面這部份的觀點。挪用好萊塢對全世界文化殖民的商品符號,以及本土文化裡表徵著庸俗之現實性格(為死人或神明表演脫衣秀)的產 品,令人難堪都來不及,有何「富文化意義」之處?「新」在那裡?至於「流動的空間」的概念,無論「金達尼號」或「油罐車」,我認為它們都只是由定點攤販改為流動攤販的形式噱頭上的變化而已。黨主席們不論是圓桌武士或郵輪船長,他們「叫賣文化」的本質不變,地攤文化的本質不變。我們的選舉美 學與政治內涵,有什麼新的內容與較高境界?
台灣的選舉,總的來說,沒有新的美學觀點與實踐。我同時也認為,選舉文化並沒有更惡質,或更吵雜髒亂庸俗功利:它原本就一直是我們的生活美學,由於持續的存在使我們視而不見、習焉不察,現在只是藉著選舉較密集而醒目的凸顯出來而已。
Related Articles (3)
總統不宜改扮造形
廖風雅(北市文字工作者)
李登輝總統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裝扮成農民、指揮官、原住民頭目、圓桌武士等造型,為該黨候選人助選,以拉抬該黨候選人的聲勢。此舉看起來像是小丑一般、有失國家元首的尊嚴,值得深思。
美國總統柯林頓、日本或歐洲國家的各黨總裁等在選舉時,都不遺餘力為該 黨黨員助選,但他們絕沒有像李主席這種不三不四的裝扮為該黨黨員助選。雖 然以黨主席身分助選是無可厚非,但是否有需要降低尊嚴,裝扮這種造型?
Related Articles (4)
政治金光秀 一場戲夢人生?
☉張小虹
在台灣過去的選舉政治語彙中,「金」的聯想總是負面多於正面,像「黑金 」、「金牛」,而今在選舉徹底電子媒體化的此刻,「金」搖身一變為「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的形象包裝、造型設計,成為「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選舉「金光戲」,政治人物粉墨登場,各以奇裝異服,創意造型為賣點噱頭,各式「化裝秀」與「變身秀」層出不窮。
於是在各個政黨努力「民主化」、「本土化」的同時,竟也無可避免地相接走上「金光化」的一途:昔日遭人唾棄的「政治是最高明的騙術」,成為今日選票保證的「政治是最高明的表演」;過去的「愛拚才會贏」,也就成了現在的「愛秀才會贏」。箇中道理甚為簡單:「作秀」與「作事」不再二元對立,「作秀」乃與民同樂、走入群眾,不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作秀」乃展現年輕人的創意與活力,以靈活取代僵化,以活潑置換呆板。
在此既展現親民作風,又凸顯年輕創意的雙重保障下,政治人物自對化裝與變身躍躍欲試。但在面對一場場的好戲上演時,我們似乎也不宜一逕跳入民主乃影像消費、選舉乃夢幻工廠、政黨乃品牌選擇的後現代政治商品消費論述。台灣不像美國一般「擬象」與「內爆」的如此徹底(政治與作秀不分,新聞與娛樂難捨,曾經是演員的雷根扮演總統,現在是總統的柯林頓偶爾客串A片演員),台灣的光怪陸離,乃是卡在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同時並置。像「金達尼號」的出場,有人稱讚其以嘉年華會的歡樂走出悲情,有人則辱罵其將歷史傷痕變成了好萊塢的電影戲服。又像國父肖像廣告的出現,有人盛讚其幽默風趣、普普天成,有人則在國父銅像前獻花哀悼,高呼褻瀆偉人。
這種對「真實」、「歷史」、「認同」的嚴重認知分裂,使得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這一場場的「化裝秀」、與「變身秀」、到底有多顛覆、多激進?「老店新開」的國民黨在秘書長章孝嚴以一襲太空人裝登台後,便是一連串黨主席李登輝的扮裝秀,從原住民裝、KMT棒球裝、圓桌武士裝到太空領 航員裝,比酷比炫、不落「人」後。而此「人」無他,自是被媒體喻為「百變陳水扁」的現任台北市長,從八四年的耶誕老人「尼古拉•伊凡陳水扁斯基」、八五年頭頂龐克頭眼戴哈雷墨鏡的「酷鴨」造型,或結合超人、麥可傑克森、宋七力的「三合一」扮相,到今年年初的「李奧納多扁」,陳水扁的變身魔力與群眾魅力一直如影隨形。
李登輝的「化裝秀」被譽為「毀神運動」,以高齡卻開放的心態取樂「頭家」觀眾;而陳水扁的「變身秀」也被讚許為顛覆傳統市長角色,從醫院、運動場晚會到街頭的與民同樂。而最有趣的是在這次年底三合一選舉中,兩人的造型「出招」道具十分顛覆的「爭議點」讓人耳目一新。像李登輝圓桌武士裝在腰上吊掛的「遮陰袋」(codpiece),乃西方男性服飾從中世紀以降一項重的配飾傳統,可稱之為「視覺化」了的「威而鋼」,既有保護更有誇示性器之用。又像扁帽工廠的創意文宣「衣著和政治都是一種品味的選擇」,一時間「品味」取代了「土地」、「情感」、「歷史記憶」、「人民」投票像逛中興百貨,選候選人像買衣服一般消費商品化。
在這裡並不想爭議「親民」是否必然「媚俗」或「媚俗」有何不妥,也不想分析不斷在政界、文化界傳播市場機制游走的一批文宣總管、創意總監是如何轉換台灣的選舉語彙和政治修辭,而是極度好奇這些前衛大膽的爭議點之出現,到底說明了什麼?台灣真的是對各種扮裝、變身已然百無禁忌,對各種族群越界,階級流動徹底開放暢通了嗎?這兩名最賣力演出的重量級政治人物,卻也同時是台灣政壇最具堅強意志,最不具妥協性格的兩位政治人物,他們的「變」,恐怕還是一種強化主體意識,以「本尊」之不變應「分身」之萬變之變,而非後現代「解構逆轉式」的虛構主體,以「分身」之萬變創造「本尊」的不變假相(本尊只是另一種分身而已)。
在戲服的邏輯裡沒有真偽,在台詞的原則下談何誠信,台灣的困境恐怕是在選舉政治已全然媒體影像化的此刻,仍有太多對前現代與現代的困惑與堅持,故而曖昧與衝突,巔狂與沮喪紛然而至。然而當這一場場金光好戲熱鬧上演時,雖不能滿足我們對扮裝顛覆與變身基進的期待,但至少提供了兩個反省批判的思考點:誰在扮裝?誰又不在扮裝?運動背心與運動短褲就比奇裝異服更「自然」,更「真實」更不像作秀的道具嗎?牧師裝就比一般的西裝領帶更「誠信」、更「道德」、更不像美麗的謊言嗎?們政治金光戲當然是選舉假期,政黨嘉年華的特權,在台灣實際運作的社會中,多少被邊緣化的「扮裝」不見天日,多少被污名化的「變身」不得翻身。政治金光戲的安全,正在於可以不中不西,不古不今,卻不可不男不女,不倫不類,這不禁使我們困惑,政治金光戲所標榜的開放流動,到底是觸手可及抑或遠在天邊的一場戲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