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林文淇
|
Film: The Sweet Hereafter
導演:Atom Egoyan (加拿大)
小說原著: Russell Banks (美國)
編劇:Atom Egoyan
 |
(律師米喬爾的過去回憶)
伊格言的《意外的春天》看似一個完全不同主題的影片。改編自羅素•班克斯(Russel
Banks)的小說,影片以一個小鎮的校車車禍為故事的中心,呈現這個小鎮的居民以及趕赴來協助/推銷法律訴訟的紐約律師如何面對這起幾乎將小鎮的孩童盡
皆淹沒的車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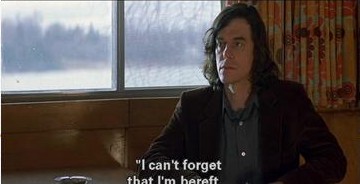 |
|
比
利目擊車禍
|
。這雖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的真實的事件,但經過小說與電影的改編,不同
的版本顯然各自從此一事件中找到所欲呈現的問題所在。小說明顯地將重心擺在美國的社會問題。從此一事件引發出作者對於幾個主要敘事者的觀察︰校車司機桃樂
瑞絲長年處於先生的陰影下,即使先生中風語焉不詳,她依舊堅持每事必問先生意見,將自己的看法透過對先生囈語的解釋來表達;越戰老兵比利妻子死於癌症,他
目擊整個事件發生經過,以及看到自己的雙胞胎兒女喪生冰川裡,原本已經對於死亡極度痲痹的他益形行屍走肉,他傳達了整個越戰老兵悲慘的經歷;妮可則是在家
中被父親性侵犯的學校啦啦隊隊長,經
|

|
|
妮
可在父親面前,決定說謊
|
過車禍她半身不遂,但因此找到對抗父親的勇氣;紐約律師米契爾則是自
己的女兒墮落離家,他責怪社會出了問題,卻不知道他自己對於社會與家庭的態度正是促使他女兒墮落的問題之一。透過這四位角色的告白,作者班克斯呈現在讀者
面前的是當代美國社會中常見的問題︰性別議題(桃樂瑞絲與中風的先生;妮可與性侵犯的父親)、越戰議題(比利的磕藥與死亡陰影)、青少年
 |
|
律
師米喬爾與女兒打電話
|
與家庭問題(米喬爾與磕藥離家的女兒柔依;妮可的家庭;比利不負責任
的父親)、現代/都市/資本主義化的議題(都市律師的大批湧入小鎮)小說以四個角色各自表白的敘事方式呈現整個故事,更讓讀者將焦點放在他的經歷與心路歷
程,由此感受到美國社會中各種問題的嚴重。
|
伊格言的電影雖然整體說來是一個十分忠實的改編,但是透過將場景由美國搬到加拿大,凸顯加拿大的自然地景的重要性外,電影改編小說更有幾個明顯不同處:角
色方面,桃樂瑞絲的女性覺醒不見、越戰退伍軍人比利由全然沮喪變成因妮可而振作、律師米喬
 |
|
加
拿大的雪地
|
爾從依舊算計、現實變成有所感動、情節、結局之社區集會去除、家庭性
侵害變成親情亂倫、結局由妮可與父親和好變成獨自在遊樂場滿足、比利之過去與死亡陰影被淡化。而且妮可的角色被明顯加重,尤其是加入一段漢姆林的吹笛手的
童話,讓整部影片加入了原來小說所沒有的一種對於加拿大後現代科技化社會的寓言內涵。這個寓言內涵與《日曆》的處理方式一樣是透過二元對比的方式來呈現︰
空間上是由一個窮鄉僻野的小鎮對比紐約所代表的後現代社會都市,透過小鎮居民間密切的感情關係來對比米契爾與女兒僅
 |
|
兩
年後的桃樂瑞絲
|
靠電話聯繫的疏離關係,也透過妮可寧願保有小鎮的和諧而拒絕律師所代
表的金錢誘惑的差別來傳達加拿大原有社會中所擁有的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活模式與價值觀。影片中米契爾所代表及象徵的都市有嚴重的磕藥、青少年問題,他隨身攜
帶的無線電話、他所深信可以解決一切的法律制度(金錢賠償),其實已經在他自己的家庭與生活中被顯現是無法處理他大老遠趕來處裡的鎮殤。小說中的米契爾在
整個事件的挫敗並未提供他反省,他依舊是原來的他。但是影片中米契爾似乎在女兒得到愛滋病後以及經歷小鎮事件後有所改變與領悟,同時影片的結尾呈現比利重
拾工作,精神抖擻地吊起象徵整個小鎮重擔的校車,另一個畫面則呈現妮可在一座五彩繽紛的摩天輪前微笑而滿足,再加上透過倒敘的方式,影片讓妮可回到車禍前
的比利家中車燈照出窗外一道彷若天堂的光線而結束,在在都顯示影片相較於小說所具有的對於未來的樂觀。 |
另外在影片的敘事(語言)方面,導演透過後設形式不斷提醒觀眾自身的觀看位置。如在片頭的橫搖鏡頭讓觀眾原以為是牆的鏡頭,最後呈現的是地板,米契爾在洗
車時做的
| The sweet
hereafter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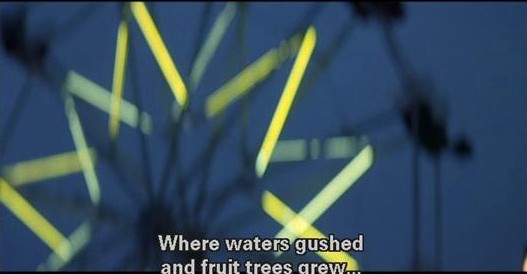 |
| and everything
is strange and new. . . . |
音樂調整並未真正影響影片的聲音,導演似乎在說「你以為你看到的就是
你看到的嗎?」而提醒觀眾能夠真正看清事物的真相。加上影片所插入寓言體式敘事與中世紀音樂,布朗寧<漢姆林衣色斑駁的吹笛手>床邊故事不得不讓我們思索
影片所要在這個加拿大的後現代社會中所提出的寓言式故事的寓意。
|
由布朗寧的詩來看,其表面意義是不誠實的代價慘痛,但詩中的意識形態上則為批判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一些價值觀。詩中的成人市官(議)員對比於吹笛手所代表
的藝術家,指出一種生產︰文化/藝術﹦現實︰理想﹦本地︰異族、兒童為犧牲品(兒童的天堂與殘障者的遺憾)的意義結構鏈。在伊格言的電影:吹笛手的故事出
現四次,後二次加入妮可的現代版本,其表面意義是小鎮莫向都市學壞(比利的訴求),但在意識型態上則暗指後現代社會中成人與吹笛手已合而為一(父親、律
師),因此原童話中的對立便成了成人所代表的科技化社會與兒童所代表的純真和諧社會的對比。妮可的勝利也正式其父親與米契爾律師的失敗,因此才有影片最後
的遊樂場的意象與天堂的光明的暗示。 |
